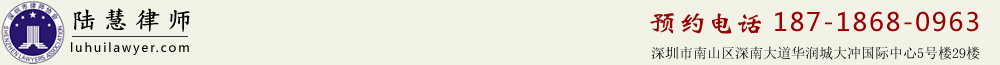刑事辯護(hù)
交通肇事逃逸后自動(dòng)投案但否認(rèn)逃逸事實(shí)的不構(gòu)成自首
深圳刑事辯護(hù)律師,交通肇事逃逸后自動(dòng)投案但否認(rèn)逃逸事實(shí)的不構(gòu)成自首
【裁判要旨】
交通肇事后逃逸,自動(dòng)投案后如實(shí)供述發(fā)生交通事故的經(jīng)過(guò),但拒不供認(rèn)交通肇事后逃逸的事實(shí)的,不構(gòu)成自首;承認(rèn)離開(kāi)事故現(xiàn)場(chǎng),但否認(rèn)存在逃避法律追究的主觀故意的,屬于對(duì)逃逸事實(shí)的否認(rèn)。
【案情】
2014年9月10日晚,王澤醉酒后駕駛摩托車(chē),搭載被害人彭明坤在道路上行駛時(shí)倒地側(cè)翻,導(dǎo)致彭明坤跌落至公路旁的坡坎下。救護(hù)人員將彭明坤送往醫(yī)院搶救后,王澤打電話(huà)讓其親屬前來(lái)頂替自己,并離開(kāi)事故現(xiàn)場(chǎng)。公安民警接醫(yī)院報(bào)警電話(huà)后趕至現(xiàn)場(chǎng),發(fā)現(xiàn)肇事者被人頂替,遂讓在場(chǎng)人員打電話(huà)通知王澤返回。王澤返回后供認(rèn)了發(fā)生交通事故的經(jīng)過(guò),但否認(rèn)找人頂替自己的事實(shí),并稱(chēng)其是為了回家擦藥而離開(kāi)現(xiàn)場(chǎng)。2014年9月12日,彭明坤經(jīng)醫(yī)治無(wú)效死亡,經(jīng)法醫(yī)鑒定系顱腦損傷死亡。榮昌區(qū)公安局交巡警大隊(duì)認(rèn)定,此次事故由王澤承擔(dān)全部責(zé)任,彭明坤不承擔(dān)責(zé)任。案發(fā)后,王澤墊付了彭明坤的醫(yī)療費(fèi)和喪葬費(fèi),并向彭明坤的近親屬賠償了經(jīng)濟(jì)損失5萬(wàn)元,取得了彭明坤近親屬的諒解。
【裁判】
重慶市榮昌區(qū)人民法院審理認(rèn)為,被告人王澤在公共交通管理范圍內(nèi),違反交通運(yùn)輸管理法規(guī),因而發(fā)生重大事故,致一人死亡,其行為已構(gòu)成交通肇事罪。王澤在發(fā)生交通事故后非但未履行報(bào)警義務(wù),反而讓其親屬前來(lái)頂替,并離開(kāi)事故現(xiàn)場(chǎng),返回現(xiàn)場(chǎng)后否認(rèn)找人頂替的事實(shí),其客觀行為足以反映其逃避法律追究的主觀故意,故王澤的行為屬于交通肇事后逃逸。王澤歸案后,雖供認(rèn)了駕駛摩托車(chē)搭載被害人發(fā)生交通事故的經(jīng)過(guò),但辯稱(chēng)是出于其他目的而離開(kāi)現(xiàn)場(chǎng),而且否認(rèn)找人頂替的事實(shí),在本案訴訟過(guò)程中一直堅(jiān)持否認(rèn)其在交通肇事后逃逸的事實(shí)。故王澤的行為不符合如實(shí)供述自己罪行的成立要件,因而不能成立自首。鑒于王澤參與搶救被害人,墊付了醫(yī)療費(fèi)和喪葬費(fèi),對(duì)被害人的近親屬進(jìn)行了賠償,取得了被害人近親屬的諒解,可以酌情從輕處罰。據(jù)此,該法院判決:王澤犯交通肇事罪,判處有期徒刑三年。
一審判決作出后,控辯雙方均未提出上訴或抗訴,該判決((2015)榮法刑初字第00093號(hào)刑事判決)已生效。
【評(píng)析】
深圳法律顧問(wèn)針對(duì)王澤的行為是否構(gòu)成自首,存在兩種爭(zhēng)議意見(jiàn):
第一種意見(jiàn)認(rèn)為,王澤雖在交通肇事后逃逸并讓人“頂包”,但并不當(dāng)然排除自首情節(jié)的成立,逃逸情節(jié)和自首情節(jié)應(yīng)當(dāng)分別獨(dú)立評(píng)價(jià)。王澤接到公安機(jī)關(guān)委托他人通知的電話(huà)后,即返回事故現(xiàn)場(chǎng)接受調(diào)查,其到案具有一定的主動(dòng)性,應(yīng)屬自動(dòng)投案。隨后其向公安機(jī)關(guān)如實(shí)交代了發(fā)生交通事故的經(jīng)過(guò)以及離開(kāi)事故現(xiàn)場(chǎng)的客觀事實(shí),其否認(rèn)找人“頂包”以及出于其他理由而離開(kāi)事故現(xiàn)場(chǎng)的辯解并不影響對(duì)其逃逸情節(jié)的認(rèn)定,因而其如實(shí)供述了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實(shí)。因此王澤的行為完全符合自首的成立要件。
第二種意見(jiàn)認(rèn)為王澤不構(gòu)成自首。
筆者贊同第二種意見(jiàn),具體理由如下。
根據(jù)最高人民法院2009年頒布的《關(guān)于處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問(wèn)題的意見(jiàn)》以及對(duì)該文件的解讀 ,成立自首的必要條件之一——“如實(shí)供述自己的罪行”是指如實(shí)交代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實(shí),交代的內(nèi)容包括“定罪事實(shí)”、“重大量刑事實(shí)”和“影響定罪量刑的身份情況”,對(duì)此應(yīng)無(wú)太大爭(zhēng)議。本案的主要爭(zhēng)議問(wèn)題在于王澤在交通肇事后逃逸,自動(dòng)投案后交代了發(fā)生交通事故的經(jīng)過(guò),承認(rèn)離開(kāi)事故現(xiàn)場(chǎng),但否認(rèn)找人頂替自己的事實(shí),稱(chēng)自己是為了回家擦藥而離開(kāi)現(xiàn)場(chǎng)。在此情況下,王澤的行為是否屬于自首。現(xiàn)簡(jiǎn)要評(píng)析如下:
1.王澤承認(rèn)離開(kāi)事故現(xiàn)場(chǎng)的客觀行為,但否認(rèn)逃避法律追究的主觀故意,屬于對(duì)逃逸事實(shí)的否認(rèn)。
關(guān)于王澤的行為是否構(gòu)成對(duì)逃逸事實(shí)的否認(rèn),主要有以下?tīng)?zhēng)議意見(jiàn):第一,王澤對(duì)主觀心態(tài)的辯解屬于對(duì)行為性質(zhì)的辯解,不影響自首的成立。依據(jù)是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《關(guān)于被告人對(duì)行為性質(zhì)的辯解是否影響自首成立問(wèn)題的批復(fù)》規(guī)定,“犯罪以后自動(dòng)投案,如實(shí)供述自己的罪行的,是自首。被告人對(duì)行為性質(zhì)的辯解不影響自首的成立。”第二,王澤如實(shí)交代了離開(kāi)現(xiàn)場(chǎng)的客觀行為,并且其提出離開(kāi)事故現(xiàn)場(chǎng)的理由并不足以影響逃逸情節(jié)的認(rèn)定,因而不構(gòu)成對(duì)逃逸事實(shí)的否認(rèn)。第三,王澤否認(rèn)逃避法律追究的主觀故意,屬于對(duì)逃逸事實(shí)的否認(rèn)。我們贊同第三種意見(jiàn)。理由如下:
(1)王澤的行為不屬于對(duì)行為性質(zhì)的辯解,而是對(duì)主觀心態(tài)的辯解,而主觀心態(tài)是案件事實(shí)的重要部分。所謂“對(duì)行為性質(zhì)的辯解”是對(duì)犯罪行為的定性,即犯罪行為在法律上是否應(yīng)當(dāng)被認(rèn)定為犯罪、此罪與彼罪等法律適用問(wèn)題所作的辯解,而不是對(duì)主觀心態(tài)內(nèi)容(是故意還是過(guò)失、是直接故意還是間接故意等)的辯解。王澤主動(dòng)投案后,否認(rèn)找人頂替的事實(shí),并稱(chēng)其是基于其他理由而離開(kāi)事故現(xiàn)場(chǎng),是對(duì)其案發(fā)時(shí)的主觀心態(tài)的辯解。而根據(jù)犯罪主客觀相統(tǒng)一的原理,主觀心態(tài)是犯罪構(gòu)成要件中非常重要的部分。沒(méi)有故意或者過(guò)失的主觀心態(tài),是無(wú)法成其為犯罪行為的。
(2)辯解理由的成立與否與是否如實(shí)供述是兩個(gè)不同層面的問(wèn)題。王澤對(duì)離開(kāi)事故現(xiàn)場(chǎng)的主觀心態(tài)的辯解已經(jīng)構(gòu)成對(duì)案件事實(shí)的辯解,其辯解理由站不住腳不能推導(dǎo)出其如實(shí)交代了自己的行為。例如,大量目擊證人證實(shí)行為人殺害他人,但行為人辯稱(chēng)自己不在現(xiàn)場(chǎng)又無(wú)法提出依據(jù),其辯解理由毫無(wú)根據(jù),但不能否認(rèn)行為人未如實(shí)供述的客觀事實(shí)。
(3)結(jié)合案件事實(shí),王澤的供述是為了否認(rèn)其存在逃避法律追究的主觀故意。王澤在發(fā)生交通事故后離開(kāi)現(xiàn)場(chǎng),主動(dòng)投案后,卻否認(rèn)自己存在找人頂替的客觀行為,辯稱(chēng)是為了回家擦藥而離開(kāi)事故現(xiàn)場(chǎng),在審理過(guò)程中又稱(chēng)是顧慮保險(xiǎn)公司發(fā)現(xiàn)其酒后駕車(chē)發(fā)生交通事故不予理賠而離開(kāi)等等。然而,王澤的辯解與其客觀行為是矛盾的,其對(duì)主觀心態(tài)辯解的主要方式和目的就是否認(rèn)自己存在逃避法律追究的主觀故意。
(4)否認(rèn)逃避法律追究的主觀故意即是對(duì)交通肇事后逃逸事實(shí)的否認(rèn)。根據(jù)最高人民法院《關(guān)于審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體應(yīng)用法律若干問(wèn)題的解釋》第三條的規(guī)定:“交通肇事后逃逸是指在發(fā)生交通事故后,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為。”王澤的行為屬于交通肇事后逃逸無(wú)疑,而逃逸情節(jié)的必要條件正是逃避法律追究的主觀故意。正如前文所述,沒(méi)有故意或者過(guò)失的主觀心態(tài),不成其為犯罪行為。王澤否認(rèn)逃避法律追究的主觀故意,正是對(duì)逃逸事實(shí)的否認(rèn)。
2.王澤到案后,如實(shí)供述發(fā)生交通事故的過(guò)程,但否認(rèn)逃逸事實(shí),不屬于“如實(shí)交代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實(shí)”。
《刑法》第一百三十三條規(guī)定,普通交通肇事罪的法定刑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,而具有逃逸情節(jié)的則升格為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,足見(jiàn)《刑法》對(duì)交通肇事后逃逸行為的打擊力度,在交通肇事案件中,逃逸事實(shí)屬于獨(dú)立于定罪事實(shí)的典型的“重大量刑事實(shí)”。如前文所述,未交待重大量刑事實(shí)的,不構(gòu)成如實(shí)交代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實(shí)。
綜上所述,王澤雖然具有自動(dòng)投案情節(jié),但并未如實(shí)供述自己的罪行,因而不能認(rèn)定自首情節(jié)。
(作者單位:重慶市榮昌區(qū)人民法院 )